

我院翻译教研室主任颜林海教授长期潜心科研,《春秋大义》、《堪城遗孤》等多部译著已正式出版。
《春秋大义》简介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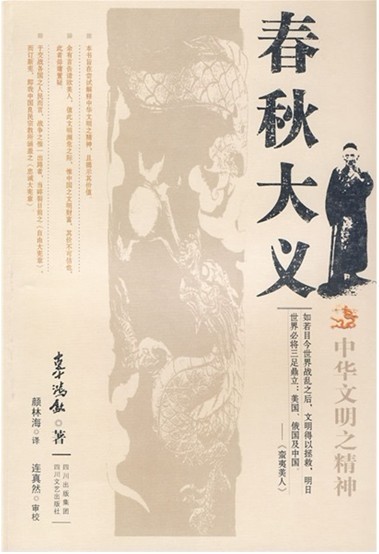
昔林海重翻译理论,而轻翻译实践。虽时有实践之作,亦仅为糊口而已,算不上真正之翻译实践,然毕竟获心得一二。历数年有余,潜心于翻译理论,尤心理学理论,今著一书,题曰《翻译认知心理学》,终得付梓,甚是欣慰。欣慰之余,更有喜极而泣之事,受出版社之约,而译辜鸿铭之《春秋大义》(又译为《中国人之精神》);恍然有杜甫之“初闻涕泪满衣裳”之欣喜。然细虑之,不知所措,无从下手,其故何也?盖因是书出于一千九百一十五年,去今已近一世矣,且须译之以文言。经“旬月蜘蹰(严几道语)”,心意已决,译!其故何也?经旬月强识辜鸿铭之文言文献,自觉可解其著文之心意、成书之意图。辜鸿铭,生于南洋,学于西洋,仕于北洋;倡春秋大义,推良民宗教;好三寸金莲而妻淑姑,喜英雄救美而妾贞子。昔之世人(即或今之世人)皆以为,其人狂妄怪诞;然若详察细读其文,窃以谓,此般俗人皆不解辜鸿铭之心愿意图。辜鸿铭乃我国鸿儒,然其论多达之以他国之语言,其旨在弘扬中华文明之大义。故译之意义甚深。译毕思之,作此序。
辜部郎学贯中西,通晓英、法、德、拉丁、希腊等外语,且能见其理极;精通马太·阿诺德、罗斯金、爱默生、歌德及席勒;真可谓“精于别国方言,邃于西学西政(罗振玉语)”。盖因其学贯中西,方可以其所长,而弘扬中国之文明。盖因其力倡弘扬中华文明,其倍受他国学者人士之敬佩仰慕,继而驰誉国际。辜部郎云,当今世界之至弊,盖因群氓崇拜教所致。欲解此困,必代之以中国良民宗教所涵盖之忠教,即忠诚之教、孔教;孔教,惟于中国文明可觅焉。然西人不解中国之言语,自当不解我中华文明之微言大义。是故,欲使西人欲领会中国文明之微言大义,有二法可行:译与论。至于译,辜部郎译有《论语》、《中庸》等,其所译者,于难解之处,必以西人名著之言语而注之释之,西人读之甚为亲切易解,故其译于西方,影响甚深。至于论,辜部郎集文成书,题曰《春秋大义》,而达其所倡。其英文文笔,流畅犀利。林语堂云,辜鸿铭“英文文字超越出众,二百年来,未见其右。造词用字,皆属上乘”。英国传教士兼学者,鄂方智曰,辜鸿铭之论著“可与维多利亚朝代任何大文豪之作品相比并”。故学贯中西,冠之于辜鸿铭,不为过也。
辜部郎怪而不诞。今之世人,览其书者,无不视其怪也。其怪不过有三。堂堂一代汉学鸿儒,却发议论以英文,此其一怪也。其所发之议论,后世之人多以为奇谈怪论,如其缠足辩、辫子辩、娼妓辩、妻妾辩、帝制辩等,此其二怪也。大凡刺讥谩骂中华文明者,必遭其反讥;受其讥者,往往张口结舌、难以驳辩,此其三怪也。其实,责辜部郎有此三怪者,窃以谓,凡此皆见浅而不见深,知其一而不知其二矣;简言之,未解辜部郎真正之用意也。其虽怪而不诞,盖因其论,由点及面、由浅及深、谆谆善诱,牵一发而动全身,阅则爱不释手,欲一气呵成而后快;阅毕则觉其言在理而不禁信之。故曰,怪而不诞。
辜部郎狂而不妄。《说文》曰,狂,狾犬也。余以为,若言之于人,狂分三类。其一、疯犬之狂。此类狂者,皆因受疯犬之伤,未早医治,而受其毒,闻水声而狂吠,见人而乱咬,迄今无药可救,九死无一生矣。其二、中空无物之狂。此类狂者,皆属虚中生势、胸无点墨,以贬他人为己之专长、窃他人之功绩而为己之所有,且面无愧色,视之当然。对其上,则阿姨奉承、摇头摆尾、犹温驯之良犬;对其下,则呲牙咧嘴、凶相毕露,犹患病之疯狗;此流人等,窃以谓,实乃卑鄙无耻、狂妄自大之人渣,迄今亦无可救药矣,虽不至于必死,然必遭人人唾弃,与死无二致焉。其三、中实大义之狂。此类狂者,皆心怀大义、刚正不阿。或勇狂或儒狂。勇狂者,临危不惧,为大义故,可抛头颅,洒热血,置之死地而后生,如今之抗震救灾之勇士。如是勇狂者,皆得人人拥戴爱护。心怀大义,刚正不阿,非勇狂者之专有,鸿儒博学之士,亦有此狂矣,余谓之曰儒狂。若有贬于其祖国文明之精微要义者,无论中外,儒狂之士必口诛笔伐,予以反驳。然其反驳也,须言之有理、证之有据。其证也,须旁征博引、左右逢源;于难解之处,必注之释之。是故,儒狂者,狂而不妄也,犹辜部郎甚是。辜部郎力倡中国之良民宗教,然良民宗教之要旨,乃忠诚教也。凡有诋毁中国文明者,无论不明中国文明之西人,抑或崇尚新学之中国新人,皆为其讥讽之对象,且其讥必有据。其所据者,常以西方名人之言而证西人或中国新人之谬,实乃以夷制夷之儒狂典范。故曰,狂而不妄。
异哉,当今吾中国之社会也!夫天下之群众,甚重其子女习西洋之语言,而远轻中国之语言;其果也,西洋之语非但未为通晓,且本族之语亦几近忘矣。悲哉,此实乃邯郸学步也。今之国人,动辄以西洋之科学衡量中国之国粹、且视之为糟粕。此类人等较之于辜鸿铭,其西洋见识,相差甚远;其国学修养,荡然无存焉。如是现象,吾辈人士当思虑之,以寻东西学二者之平衡,惟此可兴国焉。
此译成于戊子年奥运开始之日。奥运会乃世界人民之盛会,世界各国莫不争相举办,而期冀恃此以兴国运、震国威、弘文化。译者亦期冀借此奥运之机,以复原辜鸿铭欲弘扬中华文明之夙愿。
戊子年8月8日
颜林海于成都狮子山麓古道斋
按拙作《翻译认知心理学》,人之大脑所记者,命题也。所谓命题,存于大脑之非语言语音形式之意义。同一命题,可外化为不同语言形式;不同语言,亦可达相同命题。译事,犹人之穿衣也,人之本也不变,而蔽体之衣也可一日三易。命题犹人之本,语言如蔽体之衣。衣可易可变,然人之本也不变。然人之穿衣亦有讲究,孔颖达云:“体谓容体,谓设官分职,各得其尊卑之体。”简言之,人之穿衣,须搭配得当,得其体也。人之体也,不可削剔,所穿之衣也,须与体相匹配。人体之本所在何也?在其心,在其意也。人之无心,犹行尸;人之无意,如走肉。人之心,人之意,如何能解欤?闻其言、览其文也。言成句,句成文,文达心意。成句之法,语言之不同,则有不同之规;成文之法,语言若异,则有相异之矩。规矩虽有不同,然其心意不变矣。心意者,大脑所存之命题也。欲译大脑之命题,译事之步骤有六,须逐一行之。其一,命题分解;其二,命题链结;其三,命题句化;其四,句化翻译;其五,译语整合;其六,译语润饰。以上步骤,乃译者大脑认知过程之概括,序言之中,谅余不能详说;欲见其详,可览之于拙作《翻译认知心理学》。

言之于辜鸿铭,其可着西洋之服饰,亦可穿中国之长衫,然其人之本也未变。其心意,既可表之以西洋之语言,也可达之以中国之语言。语言可变,然其人、其心、其意未变矣。故翻译时,按如下译例而译。
一、总例:欲译辜鸿铭之《春秋大义》(《中国人之精神》),理解时,须览其文、记其字、体其心、明其意;表达时,用其字、仿其句、译其心、译其意。若于难解之字词,须查其典、觅其源。惟此方可译其心、译其意、且得其体也。
二、是书旨在弘扬中华文明之精微要义,故辜鸿铭于文中常引中文经典。翻译时,查引文之出处,而恢复其原貌。
三、是书旨在给昔日西人或崇洋媚外之中国人阅读,故以英语成文达意。欲使西人及崇洋媚外者信其所倡达,辜鸿铭常引西洋著名之文豪名家之言语,而证己之观点;览其书者,时有张口结舌,不禁信之。辜鸿铭所引之言语,或韵文或诗歌,故翻译时,据其所引之用意,多以汉语诗体译之。
四、是书原文颇有维多利亚时代英文之遗风,而汉语并无其对应之语言特征,今译之以文言,译文遣词造句、组句成文多以辜鸿铭之文言文献为楷模。
五、是书所涉外国人名、地名,均按《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》或《外国人名辞典》为标准。个别人名,如辜鸿铭之文言文献经常提及,则按辜氏译法翻译,且注其今译。此举旨在恢复辜鸿铭之风貌。
六、原文注释皆释以脚注,正文所涉人物,若原文未曾注释,而今疑其不明者,亦释之以脚注;凡涉及翻译及文言之出处者,皆释之以尾注。为区别故,脚注注以圈符,以序号①②③┅┅置于页脚。尾注注以框符,以序号[1][2][3] ┅┅ 置于书末。
七、另有一文《蛮夷美人》,初发于《华北正报》,后刊于美国之《纽约时报》。今之国内书刊未曾辑录,亦未曾有其译者,故今译之以飨读者,且辑于原书之后,题曰《附录二》,原书之《附录》改为《附录一》。
八、本书特于译文之后附录辜鸿铭论著英语原文,供学者同仁、翻译爱好者对照研究。
总之,译事之难,在于难解作者之心意。欲解人之心意,须闻其言、览其文。闻言览文之要旨,在于析解其命题。故译事之过程,始而析命题,再而解命题,继而译命题,终而润饰命题。译事之要旨者,译其心、译其意、得其体也。简言之,译心译意乃译事之本也。
《堪城遗孤》简介: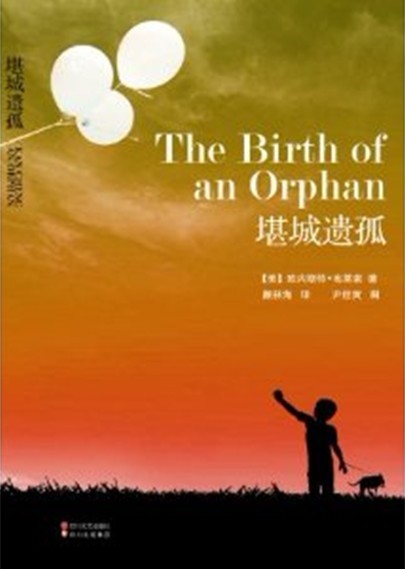
教条害人,惯例恼人。当后记成为一种教条不容更改,必害译者之审美创造,读者之审美品位;当后记成为一种惯例千篇一律,必惹恼译者读者,译者不知如何创新而烦,读者不知其中所云而恼。然而,烦归烦,恼归恼,既然又是一部译著,必然又有一篇后记,但愿读者既不烦,也不恼。
本书译者从事翻译理论研究与实践二十余年。曾想从理论上探索什么是翻译,企图寻找翻译的普遍法则,然纵观古今中外学者译者的论述,何谓翻译?学者莫衷一是,译者各有心得。本译作基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而成。至于理论,见相关论著,后记之中仅录心得概要:翻译之本质在:译其心译其意。欲译其心译其意,必先获其心或其意。欲获其心或其意,译者与作者必须心灵交融,用心灵体验作者所描绘的景象,世事的冷暖。
翻译是一种心灵交融,是译者与作者在精神上之融会贯通,合而为一。翻译过程中,译者就是作者,是作者的心,想其所想;是作者的口,言其所言;是作者的眼,见其所见;是作者的手,书其所书;是作者的腿,行其所行。唯有如此,方可获其心获其意。
翻译是一种心灵体验,可随原著人物的喜怒哀乐而喜怒哀乐。翻译过程中,没有任何世俗的功名利禄,只有纯净的意象世界。置身原著意象世界中,仿佛为其中一员,是天地,或云或雨;是山川,壑深水激;是平原,一望无际;是一草一物,一枯一荣;是春夏秋冬,冷暖更迭。是北冥之鲲,是南海之鸳雏,怒而飞,若垂天之云,观世间百态,览人间之疾苦。唯有如此,方可明作者之意图。
此本译作译自作者未曾出版的手稿中的一部小说The Birth of An Orphan。是一部典型的美国黑人作家的黑人儿童故事。其语言是典型的美国黑人语言,独特的字词用法,独特的拼写形式,独特的句法组合,独特的心灵感受,无不让译者感到为难。好在译者有幸能够与作者进行几个月的中美心灵的直接沟通,了解到了作者在“独特”背后的写作意图,也让作者了解了我的翻译宗旨:译其心译其意,并获得了作者的首肯。翻译过程中,译者时而是作者,代其思,代其书;时而化为主人公,如影随形。最终得以完成译稿。
就在我和作者通过电子邮件沟通的几个月,译稿即将付梓之时,作者却溘然而逝,未能见到自己的心血得以面世。但愿此本译作能让你了解一个美国黑人作家坎坷的童年身世。